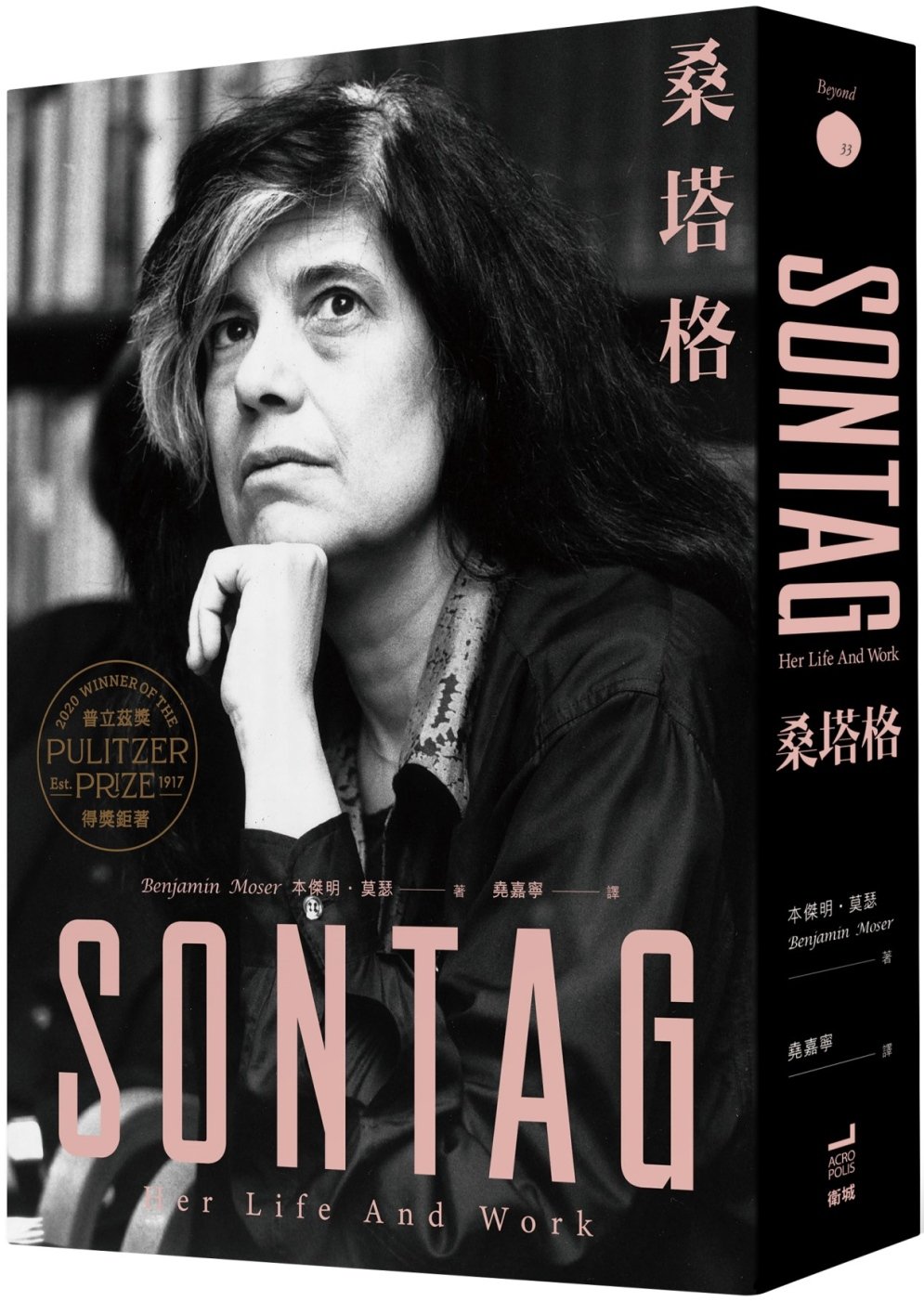1967年美國與加拿大華裔來台參加「海外華僑青年語言學習營」
因為COVID-19疫情緣故,從2020起,掀起了一波海外台裔移居台灣的風潮。他們是因為歐美疫情嚴峻只能網路上課的年輕大學生,也是帶著一家老小來台短居的專業人士。兩個月的短期計畫演變成兩年,這是我身邊不少「長期滯留」台裔美籍朋友的經驗,他們從來沒有想過來台灣會是一個選擇,但COVID-19促成了這樣的機緣,有些人就再也沒有離開了。全球疫情的不確定,歐美種族歧視的高漲,以及地緣紛爭導致人們對於未來的不確定,使得《經濟學人》曾形容「地表最危險的地方」的台灣,看起來反而相對風平浪靜。
我這一輩人,1980年代中後出生,許多都還背負著上一代的美國夢,認為有機會的話仍是必須出國唸書,最好是找一份穩定的工作,拿到綠卡移民國外。這個焦慮的背後,一方面是擔憂台灣的政治動盪,另一方面還是認為國外有比較好的工作機會。但一出國10年、20年過去,在美國待越久,不難發現這個社會仍是屬於白人的社會,作為亞裔移民,找到一份安身的工作並不難,但要融入美國主流社會,恐怕仍是需要下一個世代的翻轉。
《台北愛之船》故事的即是來自亞裔移民二代尋找認同的脈絡,某種程度上這本書的出版與竄紅(已經授權好萊塢電影團隊拍攝),體現了近年大量二代亞裔美國人透過對於亞洲的思鄉書寫,更細緻地闡述自我身分認同的風潮。
《台北愛之船》作者邢立美在美國俄亥俄州長大,如同書中主人翁艾佛的設定,父母為華裔背景移民,父親放棄了在中國的醫學學位,到美國當清潔工維生,因此希望女兒能夠申請醫學院,擁有更理想的、穩定的事業前途,但艾佛卻一心想要報考紐約大學舞蹈系,成為一名舞蹈家。這份亞裔跨世代間經常聽見的衝突成為故事的張力,不斷將艾佛推向尋找她個人價值的劇情核心。
在上大學前的最後一個暑假,艾佛的父母擅自為她報名了在台灣的「愛之船」營隊,希望她能多認識其他海外華裔青年與了解自身的歷史。中華民國政府於1967年成立「海外華僑青年語言學習營」,隸屬於救國團下,在北美、歐洲廣招華裔年輕人,作為冷戰下宣導中華民國作為「正統中國」、連結海外華僑的政治手段。
這個營隊俗稱「愛之船」,也是因為華裔人士希望透過這樣的活動,替他們的子女找到相同背景的另一半。戀愛的渴望也是《台北愛之船》書中的軸心,也因此這本書經常被拿來與《瘋狂亞洲富豪》系列作比較。某種程度上都是透過純樸亞美二代的視角,形容台北街景與商二代的往來,衝擊他們對於「亞洲」的想像,就像艾佛驚訝發現的:「台北的東西都好貴!」
在移民社群中,我們經常會提到一種常見的「老僑心態」,指的即是移民太久、與離開之地已經有文化上難以彌補隔閡的族群,他們經常會在新的國家懷念舊國之美好,而當久久回國一次,卻又無法接受原來的國度已經在各方面都有巨大的改變。把家鄉凍結在單一時間點所產生的認知上錯亂,經常會造成老僑們體驗巨大的失落感,甚至在政治上變為趨向保守的一群人。
當然,《台北愛之船》故事中的二代青年,並不是所謂的老僑,愛之船也已不再是冷戰時代的愛之船。經過多次改革,交由僑委會舉辦後,這個暑期研習營加入更多本土台灣的文化。在《台北》一書中,也能看見透過艾佛所遇見不同背景的華裔與台裔青年,帶出海外二代身分認同的複雜性。比如,在艾佛與營隊同學的對話中,即有人強調自己是「台裔美國人」,而非「華裔美國人」,兩者不能混而一談,這對於來到愛之船前只知道台灣是一個「福建外海的島嶼」的艾佛是一大衝擊,也修正了她對台灣的想像。
不過,在這些亞裔二代的創作中,多數的核心議題並非亞洲的地緣政治或國族認同,而是與他們成長背景切身相關的種族身分。台裔美國作家游朝凱(Charles Yu)的《內景唐人街》,即是用劇本形式「戲中戲」的書寫手法,描寫「平凡亞裔男」所遭遇的種族歧視,以及亞裔男性在美國大眾媒體常見的刻板印象角色:送貨人、殭屍、功夫明星⋯⋯等等,諷刺亞男難以被賦予具有靈魂並且深入的對話與劇情,更不用說被設定為「可戀愛」的對象了。
上一輩經歷過的歷史創傷,包含主角父親遭遇到二二八事件的迫害,才離開台灣來到美國,卻也只能被視為平凡無奇的唐人街餐廳服務生,游朝凱寫道:「所有亞裔男都被折疊成一個平凡的亞裔男」,精準地體現亞裔移民在白人主導社會中所感受到的流離與困境。
《內景唐人街》出版後獲得2020年美國國家書卷獎,為少數亞裔作家得到的創作殊榮,如同2022年熱賣的電影《媽的多重宇宙》,這些以諷刺視角挑戰西方對於亞裔刻板印象的作品,越來越受到大眾的關注。《內景》與《媽的》相似之處,即是它們都巧妙地挪用大眾文化中視為理所當然的亞裔符號,並充滿自覺地玩弄、翻轉這些印象。如同游朝凱寫道,種族身分的扮演,如同台前台後運作的不停轉換:
「表演者時有走火入魔之虞,假戲真做,誤以為其苦心營造的現實才是獨一無二的現實。在這情況下,我們意識到,表演者儼然化身為自己的觀眾,成了同一場戲中的表演者兼觀察者。」
──游朝凱《內景唐人街》
如何脫離種族的束縛,成為本真的「自我」,即是許多亞裔二代創作的核心關懷,如同《台北》的主角艾佛,最後透過在父親面前展現的一場舞,拒絕成為家長期待中的角色;《內景》透過劇場的設定,書寫不同代亞裔經歷的歷史。
另外,近年其他值得關注的亞美作品,包含越南裔酷兒作家王鷗行《此生,你我皆短暫燦爛》,以及韓裔混血作家蜜雪兒《沒有媽媽的超市》,皆是透過對於母親的懷念,重新審視自我的身分認同與亞洲的牽絆。我們也看見從前以離散華裔與日裔為主的亞美書寫,逐漸擴張到更多元的、包含其他東亞與東南亞作家生命經驗的故事。
從任何一個角度來說,這20年絕對是亞裔美國創作嶄露頭角的年代。在90年代前的亞美著作,比如譚恩美的《喜福會》(The Joy Luck Club)與John Okada的《叛國小子》(No-No Boy),這些在我大學時代亞美文學課程中必讀的文本,多數強調受到二戰影響而導致家庭人生破裂的創傷故事。在這些敘事中,「亞洲」不但是個回不去的遙遠國度,更是主角必須拋下才能「成為美國人」的物件。
而90年代後,隨著全球化與兩地往返越來越頻繁,亞洲的崛起,使它在大眾文化場域也更受到歐美市場的重視,針對亞美書寫的視角也相對被打開,提供了亞美二代書寫另一個時空維度的想像。
曾經,從「亞洲」作為一塊離開後就回不去的創傷之地,直到「亞洲」作為二代重建自我認同的新可能。隨著「美國夢」因為種族問題的不解、內部政治紛亂而逐漸殞落之後,「亞洲夢」似乎成為新的慾望主題,並且這樣的想望,不再是隔海鄉愁似的物化與幻想,而是一個具有複雜歷史質地,更具體並細緻的地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