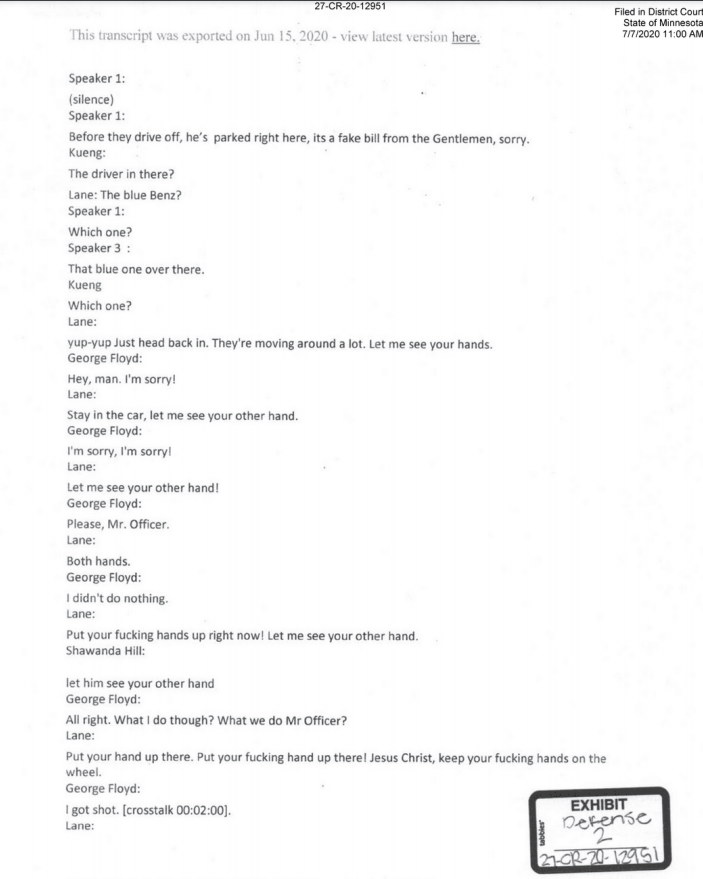原文刊登於 〈Openbook 閱讀誌〉與〈中央社〉
On Earth, We’re Briefly Gorgeous by Ocean Vuong
我在紐約下東城住的第一間老公寓裝有消防逃生梯,由外牆架在窗戶旁,攀爬整棟樓層,同時只能容許一人站立的狹窄臨時空間。它的存在是為了讓人移動,而不是停留,彷彿是一個特別為都市的人們預留喘息處,不足以稱為建築的一部分,卻是一個逃命的通路。
19世紀末,紐約市遭遇幾場奪走上百條人命的大火之後,政府決定加裝消防逃生梯這個防火裝置,但60年代後,因為許多建築家認為消防逃生梯不僅不美觀也不安全,政府最後下令禁止在新建的大樓蓋這類梯子。
雖然有人嫌它老舊並且無用,但和《此生,你我皆短暫燦爛》作者王鷗行一樣,消防逃生梯是我對紐約印象的開端。電影與百老匯劇場中,消防逃生梯經常是人們可與公共空間接觸,卻能隨時逃離的地方。它讓「黃種」、「酷兒」、「創傷」這些嚴肅題材與身分政治,以及經常承受或甚至被迫需要表白立場的弱勢人們,取得暫時、曖昧的喘息之地。
在一則訪談中,王鷗行提到當他在布魯克林大學唸書時,因為突然得知親人自殺身亡的消息,使他在紐約街頭走了此生以來最長的路。途中他不斷看到城市街景中這些無法讓人忽視的防火梯,而想:「若我們的語言裡也有逃生梯般的形體存在呢?」
作為一名越南裔美籍的酷兒作家,生於戰爭,以難民身分落腳美國康州哈特福市(Hartford),王鷗行的故事勢必與「逃難」的主題相關。一個瘦小的亞裔同志難民、不識字,甚至在成長過程中飽受自己最親密的外婆與母親的家庭暴力,他不僅在如此艱困的環境中存活,甚至成為備受國際矚目的詩人與小說家,這是所有圍觀者都想看到的故事——「啊,美國夢!」但這並不是王鷗行想說的故事。
他的第一本自傳體小說《此生,你我皆短暫燦爛》(以下簡稱《此生》)無意成為另一種模範少數的移民故事範本,而是以蒙太奇的手法,碎裂地拼湊主角「小狗」的逃難、生還、抗爭與慾望。非線性的時間敘事,破壞了我們對於「走出傷痛」療癒系體裁的渴望,彷彿他將我們帶到了建築物的消防逃生梯問:「你好嗎?我要真實的答案。」
王鷗行要帶出的對話,與最接近脊髓的脆弱相關,是不適合飯桌上的輕鬆對話,不能被單純的「我很好」給提前解決。他在書中寫到:「畢竟說故事就像吞噬。言語時張開嘴,剩下的只有骨頭——沒說的部分。」美國是個美麗的國家,但也是最暴力的地方。而他曾認為是戰爭之地的越南,卻是孕育美麗的地方。他從孩童時聽越南母親所說的寓言故事,以及哈特福農場中被囚禁待宰的小牛即知道,美好的事物將被狩獵與屠殺。你我皆短暫燦爛。燦爛只會是短暫。
王鷗行的故事中沒有救贖。小狗的母親來到康州,如同許多的越南裔難民移民,依靠著美甲坊的勞力工作謀生,對顧客說「抱歉」,因為「抱歉二字等於貨幣」。其實抱歉中的羞愧也是亞裔最常感受到的情感。在《少數派的感受》(Minor Feelings: An Asian American Reckoning),韓裔美籍作者凱西・派克・洪(Cathy Park Hong)寫到,亞裔對於自己在(美國)社會上所占據的空間經常感到抱歉,卻又在主流社會中缺乏真正的存在感,在這矛盾的處境之下,「少數派的感受」不斷發生。
美國夢的樂觀,與亞裔主體所體驗到的種族化現實,實際上有太大的落差,卻又無處抱怨,因為亞裔的人們總是不斷被告知:「現況比起以前已經好太多了。」少數生命中所體驗的落差,即是王鷗行在書中試圖說明的:語言背叛我們,只有身體與肌膚有可能成為另一種表達的方式。
《此生》書中對於性的安排總與暴力和死亡並行,我不禁想,或許慾望的身體也是王鷗行在語言的迷宮中,所細心建造的一座逃生梯。書中主角小狗與哈特福美國白人男孩崔佛的「第一次卻根本沒做的性愛」,緊緊連接在他回憶起他對幾乎徹底失蹤的父親的恨,以及6歲的小狗(作者沒有特定指出姓名,而以「男孩」取代)因為尿床,而被母親關在地下室處罰的場景之後。
地下室的濕氣、生鏽管線的蜘蛛網,以及周圍徹底的黑暗,在下一個段落瞬間移至哈特福的菸田、農倉,以及崔佛那混亂的、充滿大麻菸蒂與少年費洛蒙房間。崔佛的手指混合了「菸草、大麻、古柯鹼與機油」的味道,而臉上是電動刮鬍刀片留下的生鏽氣味,小狗從混雜並嗆鼻的味覺,以及黑暗的恐懼中找到肉體的力量與微光。他們以手握陰莖穿刺「第一次做愛,根本沒做」之後,崔佛因為自己對男體的慾望而在暗中哭泣,但小狗卻找到了駕馭身體的方式,他說:「我很快發現臣服也是一種力量。」
比起無法面對自己同性慾望的美國白人男孩崔佛,小狗說,至少這一次被幹是完全出於他自己的選擇。因為暴力即是他的日常,沒有什麼比從肉體的痛楚與被摧毀中,更能夠認識愛的方式了。
而在那之後,小狗回憶起與崔佛「真槍實彈」做愛的回憶,在書中被安置在外婆因癌症過世的章節。即使皮囊無法長存,王鷗行提醒我們,身體的感官可以被各種環境的刺激不斷提起,因為病毒攻擊而滾燙的身體,與青少年小狗和崔佛所待的農場,煤磚燃燒、滿布熱氣的密閉空間在回憶中交疊。是時候需要一座逃生梯。
王鷗行將第一次體驗肛交的痛楚、羞恥與快感,誠實並赤裸地攤在慾望面前:「我們交媾的污穢本質遂無所遁形。」而在小狗的敘事中,他不再是那名以「抱歉」取代「哈囉」打招呼的脆弱黃種男孩,他見證過死亡,他不再畏懼,只要能跨越當下的痛楚。
閱讀至此,我感覺自己彷彿與作者依靠在下東城老舊公寓的逃生梯,聽他敘述一則遙遠的回憶。他透過文字讓我們見證了他的逃逸、跌落與再起。
《此生,你我皆短暫燦爛》以小狗寫給不識字母親的書信體行文,許多深刻的情感與暴力,揉和在王鷗行似乎刻意簡潔處理的字句,卻無法掩蓋文字中的重量。如同許多亞裔美籍的移民二代,小狗試圖理解以及接近來到美國後失語的母親與外婆,透過時空交錯並零散的故事,尋找和她們重新溝通的方式,越過戰爭的創傷,與失落的期待。他對死去的外婆寫到:「我很抱歉總是說妳好嗎?其實我想問妳快樂嗎?」
也許當我們找到自己的逃生梯,即能暫時放置自身的傷痛與破壞的本能,學會不再傷害彼此的相愛方式,說出真實的故事。
此生, 你我皆短暫燦爛
On Earth We're Briefly Gorgeous
作者:王鷗行(Ocean Vuong)
譯者:何穎怡